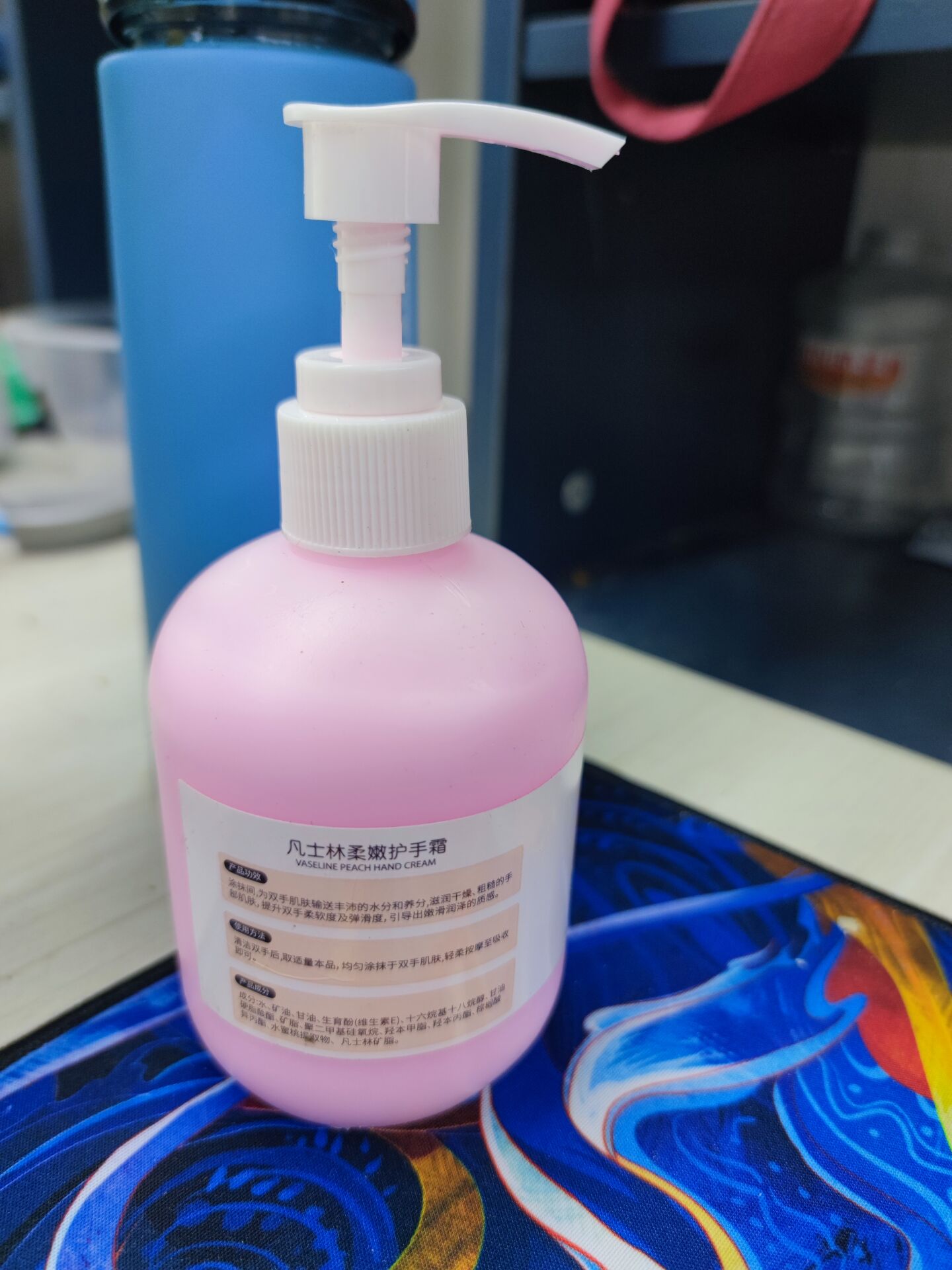“您稍等!”故宫博物院,慈宁宫往西,一扇紧闭的铁门需要刷专用卡进入,故宫博物院考古部工作人员吴伟领着记者进门,迎面是几排普通平房。拐一个弯,还藏着一道铁门。再跨进去,入眼是一地坑。
坑与坑间,有交错的土道,形成一张“谜”网。每条小道的宽度,挤不下俩成年人并肩,坑底坑壁更是“一坑一样”:有些坑里杵着一根糟木头;有些坑底铺着长方砖;有些坑壁光滑,不同颜色的土层泾渭分明。
故宫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徐海峰提前到了。同样的景,在他眼里,是百年春秋。他像是一位靠谱的时光导游,边走边聊:“这个坑底是明代的砖铺面,不过,到底是室内的还是院子里的,还没弄清楚;这里曾经有一个灶,是造办处匠人日常生活留下的痕迹;被围挡遮住的地方发现了元代的建筑构件……”
从2013年10月,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以来,类似有趣的探秘之旅累计启动了34项,但没有一个项目是意料之中的,考古人员配合着院内大小施工工程展开调查发掘,在有限的土堆里翻找残瓦断砖,清理前尘,逆转日月盈昃,拼凑还原真实的往事,为紫禁城这本厚重的书札增添鲜活的色彩。
打开“折叠空间”
将视线拉回到眼前这片大坑小坑。与大多数四壁光滑、底面平整的考古探方不同,这些坑更有个性。
徐海峰解释,宫里考古,见“面”即停——一旦发现了重要的砖面、地面、活动面,就暂时不再向下清理了。古今重叠型的建筑考古,去除表土都是遗迹。目光所及,每一个保留下的面,都是一段鲜活的记忆。
这种讲究,只是故宫考古必须遵从的铁律之一。“不主动动土”“考古主要利用前代施工形成的各类施工坑、埋藏坑、废弃坑来判断地层和堆积状况,只在局部解剖发掘至生土”“提前介入,随工记录测绘、视发现遗迹现象不同情况,分别进行短期清理调查和长期考古发掘”……苛刻、严谨的规定背后,是考古人员对文化遗迹的珍重和敬畏。
在这处考古工地西边,一墙之隔是慈宁宫花园东院。对观众开放前,这里也进行了一场研究性考古发掘。那次“微创手术”总共发掘了约670平方米,只有两个小创口,长宽分别是1.7米、1.2米,1.2米、1米。
摊子铺得不大,但成果令人惊喜。这也是故宫博物院首次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并证明了紫禁城西路区域内有一组规模宏大、地位重要的明代早期宫殿建筑基址——据判断是明永乐时期大善殿的地基。
正在进行的考古项目,也是一次类似寻缘续梦的过程。考古工地的已知档案和考古成果被制成展板,摆在门口,上面有这样的介绍:“故宫造办处遗址考古项目,位于故宫外西路慈宁宫东南、内务府以北区域,今故宫修缮技艺部办公区。在明早期此处记载不详,明晚期该处被认为是司礼监经厂直房所在地,为存储日用纸札书籍的地方。清初将养心殿造办处部分作坊挪设于此,故称内务府造办处。”
经过1年多的考古发掘,暴露出的砖石、泥土,佐证并丰富着展板上的文字。
“这是一处清代踏跺的遗迹。”徐海峰脚下是一块青白石,长条形,表面风化严重,没有雕刻花纹,有点类似于现代人住宅门口的过门石,不仅有台阶的功能,还有助于处理从建筑内到室外环境之间的过渡。畅想一下,几百年前,一位造办处的匠人在思路枯竭时,也曾站在这里,眺望着红墙上起伏的琉璃屋顶。
跨过踏跺,跟着徐海峰以步量“屋”。“这座建筑面阔三间。”徐海峰引经据典,在《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造办处的格局和建制,有琉璃屋面尖山式硬山建筑和布瓦屋面卷棚式硬山建筑。现在考古发现的是后者的遗址,体量与记录相同。更直白地说,这里曾经有150余座房子,排排相连。大多数房子和北京胡同里的普通民居一样,墙面白色抹灰,灰瓦如鳞。
在考古现场转一小圈,一个“折叠空间”徐徐展开——
去掉脚踩的一层砖,往下探大约20厘米,红砖水泥痕迹以及一些弯曲的钢筋是现代的记忆。上世纪五十年代,故宫工程队(现修缮技艺部前身)在这里办公。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造办处区域早已荒废变成了遗址,故宫从民间请来能工巧匠,在这里扎根,请他们边修缮边带徒,开启了自辛亥革命以来故宫的首次大修。
清造办处时期的遗迹,通过房址地基判断这里主要是排房。“屋”旁有一条蜿蜒的排水沟,形制和慈宁宫花园东院发掘出的并不一样,不是工艺精良的龙须沟,这应该是为造办处的工作单独加砌的。
清代往下即是明代,各种铺法不同的砖铺面暴露出来。依据以往考古的资料和经验,有一片地面年代可以追溯到明中后期,与慈宁宫花园东院发现的明代地面可以“连”成片儿。
更早的记忆要追溯到元代,目前找到了二十多件建筑构件,有绿色琉璃瓦吻兽、脊饰,也有印着花纹的方砖。是旧时宫殿留下的线索还是匠人扔的建筑垃圾,尚不得而知……
砖、瓦、土,在考古人的眼里都有生命,会说话。
不过这些描述,是经过简化提炼过的。真实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历朝历代的文化层叠摞着,甚至会有“后来侵入”的现象,“因此,判断相对年代都要有依据,主要靠土里包含物和层位关系来断代,和它所处的深度没有必然的关系。”徐海峰说。
物事见人心
在复杂且有限的空间里,找寻韶华一瞬,靠的是精耕细作。
造办处考古现场,徐海峰隆重推荐的“景点”是一个实心“积木”——由长条砖石砌成的一个方柱体。它的学名是磉墩,是屋殿中柱子的地下基础。慈宁宫花园东院遗址也发现过类似的磉墩,但造办处的这个磉墩几乎比它大了一倍。
经过考古发掘和后续研究,明初的建造工艺被抽丝剥茧地还原了:建大宫殿前,工人先挖一个斗形的大坑,俗称“满堂红”,学名基槽。之后在坑底磉墩的位置打上木质的地钉,上面用云杉和柏木绑成扎实的“竹排”铺好。再用石板平铺错缝打造平整的桩台,台上建砖砌的磉墩或墙基,周边以一层夯土一层碎砖瓦层层夯筑起来。就这样一层压一层,宛如一块“千层蛋糕”一样填满基槽。“磉墩上是柱础,之后才是柱子,这样建成的大殿非常牢固、稳定,这是皇家建筑能墙倒屋不塌的原因之一。”
新露脸的磉墩用统一规格的大型灰砖按“回”字形铺砌,长约4.45米,宽约4.4米,高约1.65米。“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大体量的砖砌磉墩。”吴伟是一名年轻的考古队长,参与了明中都的考古遗址发掘,他说,“在安徽省凤阳县发掘一号宫殿时也有类似规模的磉墩出土,不过是用夯土和碎石片夯筑成的。可见故宫的建筑更讲究,更坚固,更规范了。”
徐海峰说:“这应该是明代永乐皇帝建造紫禁城时的一座建筑遗存。”
这座宫殿会是什么样?徐海峰原地为轴,分方向讲:“往西南,先发现了体量一样的磉墩,之后在东南角也找到了一个……最终凑齐了四个磉墩,测量它们的中心点间距,发现基本是等距的,间隔11米。”
在古代,四柱围一间,一座宫殿建筑的柱子远远不止四根。这座明初建筑一个开间的面阔、进深均达11米,足以推断,宫殿体量巨大。
不过,真正有多大,还是要往地下看。工作人员利用剖面、沟槽弄清楚层位关系,在周边钻探找“边儿”。历时约两年,大殿东边界找到了,依据是发现了东侧台明的基础。解释一句,太和殿等中国古代宫殿都是建在台基之上的,台基露出地面的部分就叫台明。“往北也找到了东侧基槽的边缘,这也是边界判断的依据。”
其他两个方向,还没定论。“明年开春,我们会继续往西找,希望将大殿的平面布局尽可能补全。”徐海峰说。至于往南,注定此次“无解”,因为目前的考古发掘是从南往北推进,几乎贴着墙根开始的。
“当然会有遗憾。但我们的工作是做好手头的事儿,有些机会就是留给未来的。”徐海峰说,由于明早期对故宫西路的格局记载比较模糊,所以目前还不能完全判断这座宫殿的“身份”。
在故宫考古就是这样,从上到下、由晚到早,一层一层的揭秘,随物应机。
这种状态和变化与古代匠人不谋而合。同一片考古现场,清代的磉墩就随意得多,砌砖中掺杂着半砖和残砖块。而明初的磉墩坚固程度当得起“千年大计”。“考古发现,清代的建筑基本没有破坏这些明代基础,应该是有意识的利用,干脆直接在明代房址上盖房。”
新旧更迭,盖房、考古亦如人生,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一次考古,怀揣匠心的考古人拉近数百年时光,让我们有机会透过最普通的砖和土,感悟匠心。
为历史“拼图”
通过考古发掘,晦涩平铺的史料记载不断翻“新”。
在南三所区域对宫殿基址的发掘,可以看出雍正以后不再预立太子而发生的政治制度变革反映在了建筑规模上,即曾经的太子居所面积缩减。南大库旁清代御窑瓷器埋藏坑遗迹,揭秘了皇权制度下对于专属物品的严格管理制度。东城墙根儿下找到明永乐时期的地面,意味着今天故宫的地面普遍抬升了约1米……
造办处考古现场最北侧,被围挡包裹得严丝合缝。这里出土了一批元代的建筑构件,有吻兽和脊兽残件,也有瓦和砖。有些构件上,三爪龙纹图样清晰可辨。
这不是第一次在故宫发现元代的痕迹。在隆宗门西侧,也发现过元代的素土夯筑层和黄土层交替夯成的夯土地基。这处叠压关系清楚的元明清遗迹,被称为故宫“三叠层”。徐海峰说,关于元大内、燕王府、西宫、紫禁城空间地望、沿袭关系等,学界目前并无一致意见。“现在这些考古发现,对于研究元大内格局、紫禁城历史和中国古代建筑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当时,考古人员在明代早期夯土层里也发现了一些元代建筑构件的碎片。不过根据数量和状态推测,它们只是明初营建时混杂进去的。徐海峰说,这次发现的情况不同,元代建筑构件在堆积层中密集出现。但究竟是元代建筑的遗存,还是匠人堆放建筑垃圾的地方,都是未来研究的话题。
“考古就是这样,有新发现,但发现的新问题会更多。”吴伟说,解决问题则需要多学科、多样化的手段,努力做到“颗粒归仓”。
甚至连考古后的回填,在故宫都立了一堆新规矩。以隆宗门和长信门遗址回填为例,考古人员对暴露在自然环境下的遗存进行环境监测,发现1月中下旬至2月初,坑内温度基本在0℃以下;温度最高的是墙基上部和底部大约3.4米的点位,平均温度在6℃左右。
类似的科学检测和分析完成了一系列。一组组数据汇总成一张张曲线分析图,目的是给遗迹“看病”,在回填时进行“诊疗”。徐海峰说,回填时采取原土、原工艺,该夯筑的地方也会夯筑,对局部区域则重点加固并标记。“未来如果有需要,随时可以快速清理,实现展示的效果。”
考古人员还利用全站仪、RTK(实时动态测量技术)、三维激光扫描仪、倾斜摄影等仪器、方式,对探方遗迹进行测绘、记录,全面保存遗迹的数字化资料。
造办处考古现场,吴伟指着探方上搭建起来的保护大棚说:“每一次考古都会进行数字影像基础数据采集,每次也有创新,比如这回搭建顶棚时特意选择了磨砂质地材料,既透光又不会太晃眼,以减少阳光变化对图像数据带来的影响。”
故宫考古不光关注地下,也关注地上。故宫大高玄殿研究性修缮保护项目中就首次尝试将考古类型学和地层学的理念运用到古建修缮中。通过“解剖”屋顶,考古人员“发掘”记录了灰背等信息,运用科学方法对泥瓦分类进行检测,对斗拱、大木进行考古类型的排比、记录和研究,获取了以往研究中从未发现的重要历史信息。
有新意的考古,每次都像是解谜。但真正想看透紫禁城的地下迷宫,考古人员想了个讨巧的办法——拼缀复原,见微知著。徐海峰说,紫禁城里的考古,发掘地点都是被动确定的,发掘面积小,而且不能随意扩大,这意味着揭露出的遗迹可能做出多种推测。为了改变这种管中窥豹的困扰,只能靠数据资料的积累和分析,久久为功。
考古人员将故宫视为一个大遗址,参照《故宫保护总体规划》,以历史功能为依据将故宫保护范围划分为48片相对独立的院区,编制遗址代码和探方、探沟号,同时将不同区域的土质土色、包含物、营造方法等记录下来,结合地质勘探、地理信息和砖石数据库建设,像拼图一样逐步复原某一区域乃至整个紫禁城的沿革与布局。“总结出的不同时期宫殿、墙基、门道、石桥等各类遗迹的营建工艺,也可以为后续考古调查和发掘提供参考。”
截至今年年底,34块拼图已经解锁。未来,宫里寻故,还将带来更多惊喜。也许到某一天,八方来客走进这座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群,能看展览,看建筑,也能看厚土里承载的六百载。
(原标题:宫里寻故)
(记者:刘冕 吴薇)